 打印本文
打印本文  关闭窗口
关闭窗口 三四 弟子篇--饭沼
“怎么样,好看吧。”听见律师先生在跟我说话,我马上转过身,隔着饭桌在他
对面坐下:
“太好看了。来日本这么久,今天是头一次俯瞰东京的夜景呢。要有照相机,真
想拍下这一切来。”
“以后还有机会的。呶,这是菜单,喜欢什么随便点吧。”
我翻开那本大相册般精美的菜单,匆匆一翻,全是几千块钱以上的菜,这怎么吃
得起?!
“哎呀,这实在太贵了,咱们还是去吃便宜的吧!”
他大笑起来:“你这个人真有意思。好吧,看来只好我随便叫了。”他把服务员
招呼过来:“那种各色各样菜都有的套菜,有吗?来一套,再来一瓶啤酒。”
香喷喷,热腾腾的擦手巾送来了,接着又是红绸子绣花的餐巾,杯,碟,勺,筷
,碗一一给我们摆好。女服务员全都穿着大红的旗袍。不知是那衣服裁的不对还是
她们的身材不对,反正怎么看都别扭。
啤酒来了。服务员为我们斟满了杯,退下去。律师先生立刻朝我举起了酒杯:
“今天见到你这样一位中文老师,非常高兴。今后请多多关照!”
我也举起酒杯:“也请您多多关照!”
菜,一道一道地上。鸡,牛肉,虾,鱼,豆腐,青菜,我爱吃的东西全来了。能
够如此开荤,实在大喜过望。我大口大口地往嘴巴里塞,把文明礼貌之类全抛到九
霄云外去了。他见我吃得这么过瘾也挺高兴。他一边拼命往我的盘子里夹菜,一边
说:
“吃吧吃吧,不够再要。今天就是要让你吃痛快。”
闹得我有点不好意思了,觉得自己活象个刚进大观园的刘姥姥。
“你平时都在什么地方吃饭?”他斯斯文文地吃着问我。
“要不在学校的食堂,要不在打工的店里。”
“吃的怎么样?”
“学校的饭便宜,不好吃也吃不饱。打工店里的饭不错,管饱。”
“打工一个小时多少钱?”
“现在是七百块。”
“太少了,”他同情地摇一摇头:“简直少得可怜。”
“可我这还算是高的呢。”
“那么你教中文一个小时多少钱呢?”
我知道今天的谈话马上就要进入关键。然而我向来羞于谈这个问题,开口向别人
要钱,多不好意思。我迟疑了一下,说:
“当然要比打工多。可是每个学生给我的都不一样。有的多些,有的少些。”
“那么目前给你最多的学生,一个月给你几万?”
“岛本给的最多,一个月给我三万。可她是每周上两次课。”
“好的,知道了。那么,从今以后我每个月给你五万块,也是每周上两次课。同
意吗?”
我甚至疑心自己耳朵出毛病了,直盯着他的脸:
“您是说,五--万--块?”
“难道还不够吗?”
“不不不,我是觉得太多了太多了。”我慌忙摆起手来。他又一次大笑了:
“我一眼就看出来你是个好孩子(管我叫'孩子'),是一个模范的中
国留学生('模
范'),又挺可怜的。这五万块钱如果能够帮助你,我感到很高兴。那么,这件
事咱
们就这么说定了。接下来,那可就要看你的了,当然也得看我的。”
“能不能告诉我,您为什么要学习中文呢?”我总是不能不问这个问题。
“因为日本还没有一个懂中文的律师,我要作第一个精通中文的日本律师。”他
的表情和声音都显示着不容置疑的坚决。
“律师难道有必要懂中文吗?”我又问。
“以前也许没有。但是今后,一定会有,没有不行!世界在变,懂吗?”
噢--我,懂了。
我们的学习就这样开始了。每个星期两次,或在他那布置得如同艺术画廊般的事
务所,或在我们学校空荡荡的大教室,或在饭店,咖啡馆,或在商店,大街上。处
处都成了我们的课堂。就连走路,乘车,喝茶,吃饭……一抬手一投足,都要同学
中文联系起来。
我很快就发现律师先生不仅记忆力好,求知更是心切。看见什么问什么,碰到什
么学什么,不厌其烦。而且任何一个词汇或句子,顶多教给他三遍,他便能牢牢记
住并从此使用起来。我们的学习进行到第三个月的时候,他已经能用不少中文词汇
跟我讲话了。进步之快确实令我佩服。而他,越学越有劲头,立刻又提出要到北京
实地学习。
在北京那短短的五天时间里,他几乎无心参观浏览,而是一门心思学中文,说中
文。
到北京的第二天,我带着他参观完故宫,从正对着景山的故宫大门出来。他看见
沿着筒子河有许多摆小摊的,立刻大喜着跑过去。我知道他又想跟人“练一练”了
。
几个摆摊子的农村姑娘见他这么急匆匆地跑过来,以为他真的要买什么,一个一
个都争着对他喊:
“吃包子不?热包子!”
“冰糖葫芦,又酸又甜!”
“热牛奶,又鲜又好喝哟!”
“茶叶蛋,要茶叶蛋不要?”
他跑到摊子边突然又发起愣来。我知道他是没听懂姑娘们的话,她们讲得太快又
带着口音,况且其中不少名词都是他没学过的。我连忙走过去想帮他一把,刚用日
语说了一句:“那是……”他立刻不耐烦地冲我一挥手:“不要!不要!”好,那
我看你自己怎么办。我索性一闭嘴,袖手旁观。几个小姑娘见他熊我,全都嘻嘻笑
起来,还不知道他是个日本人呢。
他站在摊子前看来看去,可惜半天也没找出一样他叫得出来的东西。这时他的眼
睛停在了亮晶晶的冰糖葫芦上,用手指着问:
“这个东西能吃吗?”
“咋不能呢?糖葫芦嘛!”几个小姑娘咯咯直笑。
“你说什么?”他也不在乎人家笑。
“我说'能--吃--'。”终于发觉他不象中国人了。
“我买。多少钱?”
“这边儿的两毛,这边的三毛。”
“很便宜。”
“买几根?”
他回过头来看看我:“你吃吗?”
我摆摆手,并告诉他:“这个东西是酸的,你也许不爱吃。”我把话讲得很慢。
“是酸的?”他问小姑娘。
“不酸不酸,甜的。”姑娘生怕他不买。
“给我一个甜的,不要酸的。”
糖葫芦刚到手,旁边的姑娘又招呼他了:
“吃包子不?热包子。”说着把盖在笸箩上的被子一掀,露出一大堆冒着热气的
包子来。
“这叫'热--包--子'?好吃吗?”
“好吃呀,买个尝尝。”
“好的,我买两个热--包--子。”见跟姑娘们对上了话,他高兴极了。
“在这儿吃还是带回去吃?”姑娘又问。
“请再说一遍,我不懂。”
“你拿--回--家--去--吃--吗?”
“为什么我要拿回家?我的家在日本,大后天才回去。”
姑娘们一个个乐得前仰后合。卖包子的姑娘立刻给他搬来一个长凳子让他坐,又
把包子盛在一个盘子里搁在他面前。
我走过去:“冰糖葫芦我帮你先拿着吧。”我不敢再对他使用日文。
“你帮我拿什么?”
“这个东西,”我指指他手里举着的糖葫芦:“叫冰--糖--葫--芦。”
他懂了,一面把东西交给我,一面把这个名词重复了三四遍。于是我知道,这个
词他从此不会再忘记了。
“我要一杯茶,有吗?”他咬了一口包子,问小姑娘。
“有,二分一碗。”她的活音刚落,卖牛奶的姑娘着急了:
“这儿有牛奶,喝一碗不?热呼呼的。”说着打开锅盖,高高地舀起一大勺叫他
看:“瞅瞅,多稠!”
“啊,牛奶!好,好!”他兴奋地喊起来。
老大一碗热牛奶又摆到他面前。他喝了一大口:“好喝,很好喝!中国的牛奶比
日本的好。”喝完一大碗,他又要了第二碗。一边吃着,喝着,还一边兴致勃勃地
跟几个姑娘左一句右一句地练中文。
看着他满脸带着北京春天的风尘,坐在大马路边一条粗糙肮脏的板凳上,既没有
红绸绣花的餐巾,又没有香喷喷,热乎乎的擦手巾,使用着既不好看也未必清洁的
粗瓷大碗,却是那么愉快地吃着,喝着,说着。我突然觉得这位聪明好学而素来令
我敬而远之的大律师先生,与我的距离悄悄拉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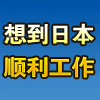
 打印本文
打印本文  关闭窗口
关闭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