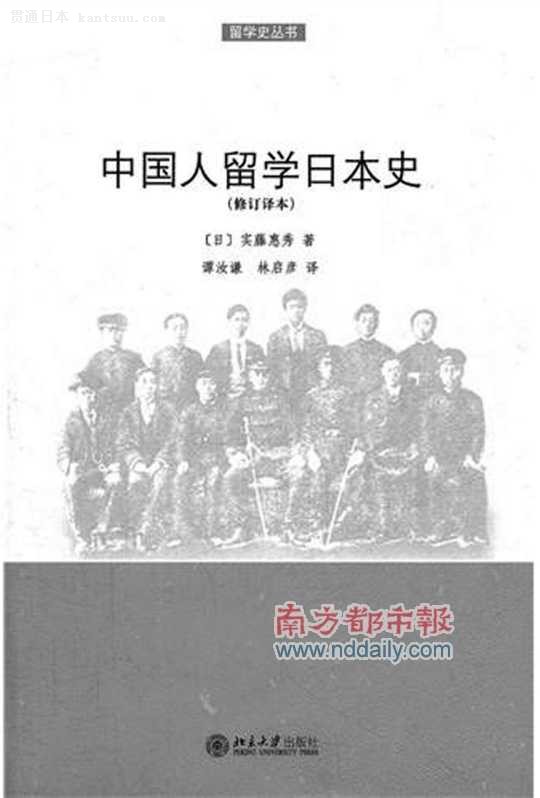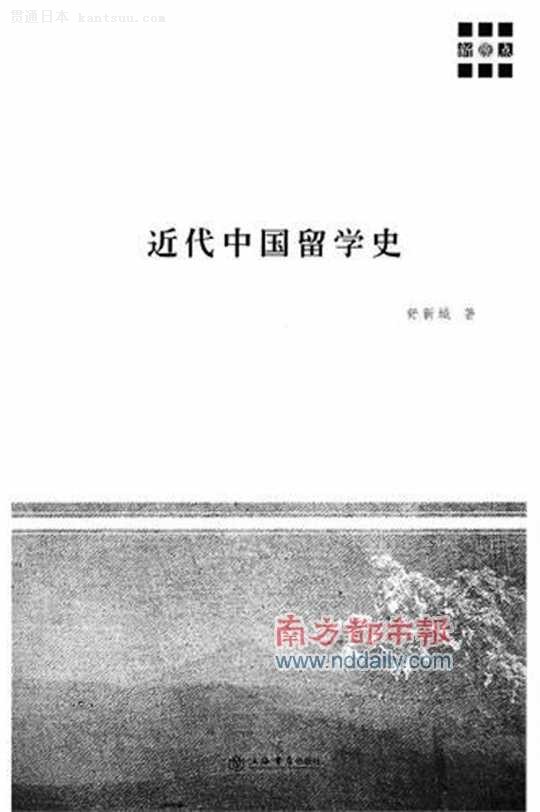《中国人留学日本史》,(日)实藤惠秀著,谭汝谦、林启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4月版,49.00元。
延伸阅读 《 近 代 中 国 留 学 史 》,舒 新 城著,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5月版,21.00元。
《新政革命与日本》,(美)任内著,李仲贤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7月版,24.00元。 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明治二十九年)旧历三月底,由清廷派遣的13名中国留学生抵达日本。这批留学生年龄从13岁到32岁不等,均经过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考试选拔,是人中翘楚。这件事具有破天荒的意义,一部近两千年的中日文化交流史,从此改写:日本从留学生派遣国一变为接受国,而中国则从留学生教育国“沦为”派遣国。 从“支那”到“中国” 派遣留学生并不羞耻,之所以说“沦为”,是因为事件标志着两国文化地位的逆转。古代中国,文明灿烂,以印刷术、指南针、火药、穹窿建筑等自有“知识产权”为代表,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具体而实在。“近世”(为便于比照,此处权且用日本史的术语,指江户时代)以来,中国对外部世界的文明辐射渐弱,崛起的西方对东方的“逆辐射”渐强。而这种西方文明自西向东的“舶来”,即所谓“西学东渐”,最初的重心并非后来成为西方世界(政治意义上)一部分的日本,而是中国。而以明治维新为开端,中日两国在一系列重要环节上开始拉开距离,从制度文明到社会文化,从金融经济到教育民生,日本均领先于中国。 而恰恰是这种落差,构成了中国向日本派遣留学生的动力。如果考虑到首批派遣是在《中日马关条约》签署(1895年4月17日)的翌年,这种动力有多大便可想而知。可是,首批赴日的13名留学生中,竟有4名在抵日两三个星期之后擅自离校归国。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他们觉得东洋食物难以下咽,唯恐危害健康;二是频频受到日本小孩子“猪尾巴,猪尾巴”(C hanchanbouzu[坊主]或C hankoro[],是明治时代日本人对中国人的蔑称,意为拖着猪尾巴发辫的秃子)的嘲弄,精神上难以承受。前者基本上是生活习惯使然,未必是真问题,后者却意味着现实的压力。大正时代(1912—1926)以降,问题非但没有得到缓解,反而变本加厉起来,“支那”、“支那人”、“支那鬼”之类的称谓,让留日学生们越来越“伤不起”。 从语源上说,“支那”源自“秦”(C hin)的音变,印度在梵文的读音后加上母音,向东传回中国,向西传向欧洲。在欧洲,中国被称为“C hina”或“C hine”;唐代的中国僧侣赴印度修习佛法,在当地听到别人对自己国家的称谓即为“C hi-na”。后佛典汉译时,中国便被表记为“支那”(或“至那”、“脂那”、“震旦”、“振旦”等),并随佛典东渡日本。江户时代中期以后,开始成为指称中国的专用名词。因此,这个词汇本身原本是中性,并没有后来的意识形态化色彩。孙中山、黄兴等人都曾在文章中不经意地使用,梁启超则用“支那少年”做笔名……这个词的“变味”是从与日本大陆政策的“捆绑”开始,在日本民族主义坐大成帝国主义的过程中,终于发展成对中国和中国人的人种学意义上的蔑称。对此,实藤惠秀写道: 日本国策使一般日本人的眼光刻薄起来,经他们说出的“支那”一词令人难以容忍,留学生坚决反对这个词汇,而日本人也顽固地予以反驳。这个国号问题,简直是留学生与日本人之间恶劣关系的象征。只消翻一翻郁达夫、郭沫若等人早期的小说,便能看出这种蔑称对当时生活在东瀛的留学生的心理折磨到了何种程度。 在整整两代留日学生持续的呼吁、抵制下,1930年5月,民国政府正式对外交部发出训令,向国际社会表达了坚决禁绝“支那”称谓的严正立场和决心: 中国政府中央政治会议鉴于日本政府及其人民以“支那”一词称呼中国,而日本政府致中国政府的正式公文,亦称中国为“大支那共和国”,认为“支那”一词意义极不明显,与现在之中国毫无关系,故敦促外交部须从速要求日本政府,今后称呼中国,英文须写“N ational R epublicofC hina”,中文须写“大中华民国”。倘若日方公文使用“支那”之类的文字,中国外交部可断然拒绝接受。 可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中方的抗议、表态不仅无法奏效,反而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经主流媒体报道后,日本国内甚至掀起了一场针对中华帝国自古以来以华夷秩序凌驾于“夷狄”之上的“傲慢敌国”的舆论反制。尽管不乏左翼文化人和媒体的呼吁、努力,但真正的转机还是在战后:1946年6月,日外务省以外务次官的名义发表《关于避用“支那”称呼事宜》的通知,对各新闻杂志社、出版机构的对华称谓问题作出行政指导。一个月后,文部省如法炮制,以文部次官的名义转发该通知精神,对所属各大学和专门学校等教育机构作出指导。直至1949年10月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支那”才从日本的大众传媒和出版物中绝迹。用实藤惠秀的表述:“从此,即使政府默不作声,"中国"一词也会从日本人口中溢出;而"支那"一词,明治以来运用的次数也许较"中国"一词为多,但无论如何也已注定成为日本语言中的死语。留学史中的"支那",却不幸地一直成为日本人与中国留学生纠纷的死结,直到留学史闭幕才结束。” 可吊诡的是,1949年10月以后,日本人虽然不再称中国为“支那”,但却制造了一个新名词“中共”,作为日舆论界称呼中国共产党治下国度的专用名词。直至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日主流媒体才取消“中共”的称谓,一律改称“中国”。从“支那”到“中共”,再到“中国”,微妙地折射了近代以来,日人在想象和面对大陆邻国时心态的变化。 “文化反哺”的功罪 自1896年首批留学生赴日以来,留学生人数逐年增加,至1905、1906年间达最高峰(8000名左右)。美国学者任达(D ouglasR . R eynolds)在《新政革命与日本》中说:“粗略估计,从1898年至1911年间,至少有2 .5万名学生跨越东海到日本,寻求现代教育。” 与此同时,大批日本人应聘到中国内地学校出任教师(称为日本教习),或在各类政府机构中担任顾问(军事、外交、教育、农事顾问等)。除此之外,日人还在中国内地开办学校(如杭州的日文学堂、南京的同文书院、北京的东文学社和上海的留学高等预备学堂等),派遣日本教师授课,在中国本土开展日语教育,培养留日预备军。赴日留学生的增加与赴华日本教习、顾问派遣规模的递增成正比,同消同长。 历史地看,赴日留学潮无疑是现代史上最重要的文化交流运动。其过程长且复杂,包括实藤此著在内,海内外相关著作已多有阐述,在此不赘。姑且就其影响问题,略论一二。 若用一句话来定性地加以概括,也许可作如此表述:如果没有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两国文化地位逆转之后日本对中国的“文化反哺”的话,那么包括笔者此刻谈论该问题的拙文在内,一切要么是“无从谈起”,要么则须彻底变换形式(包括文体、文法及绝大部分学术专业名词)。因为,涉及现代社会文化思想的一整套学术术语几乎全部来自日本语,诸如国家、政府、革命、自由、民主、人权、共和、宪政、政治、经济、商业、法律、文学、美术、戏剧、音乐、抽象、乐观、形而上学、意识形态,等等。试想,如果从一篇用现代行文表述的学术论文或讲演词中把从日文中舶来的词汇术语统统过滤并加以置换的话,意图将何以表述,读者或听众又将如何接受呢?即使不是“无从谈起”的话,“不知所云”怕是唯一可行的结果。 对此,从汪向荣的《日本教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10月版),到美国学者任内的《新政革命与日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版),包括被认为是该领域最权威著作的实藤此著在内,均对日本的“文化反哺”在中国现代化中的作用持正面、积极的评价,甚至视其为一桩绝对的好事。 但反思的声音也并非没有。如舒新城早在1928年出版的《近代中国留学史》中曾发出过“军阀如此横行,留日学生自应负重大责任”的慨叹:“五四运动”史权威学者周策纵也曾注意到“留日的中国知识分子所受军事主义、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影响,较留学其他地方的学生所受的为多”的现象。 就笔者视野所及,在这方面做出最深入反思的是中国学者王彬彬。他在《近代以来日本对中国“文化反哺”的反思》(见《风高放火与振翅洒水》,王彬彬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2月版)一文中指出:“从日本输入的"西学",已远不是原汁原味的西学,而是被日本所删节、改造、扭曲了的东西。”对于接受了如此强劲的“文化反哺”的中国何以竟未能转型为一个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宪政国家的问题,他认为:“或许正因为日本的影响过于强大,换句话说,或许正因为在中国的现代化刚刚起步时,就误投了师门、错找了奶娘。” 也未可知。但正如现代化进程之不可逆一样,真正的悲剧在于,即使这种“文化反哺”是“狼奶”(王彬彬语),我们却已吐之不尽。 本版撰文:刘柠(学者,北京) 回顾 逆转和落差 1549年,西班牙传教士方济各(Francis Xavier)到日本传教。但他很快发现,日本的文化来自中国,日人对中国极为崇尚,“倘使日本文化的发祥地中国,也信奉基督教的话,日本亦必步其后尘”,于是打算离开日本,改赴中国传教。可他后来未能如愿,两年后病死于上川岛。这个在日本家喻户晓的故事表明,“不论在经济上或思想上,西洋人都以中国为目的,日本并不怎么重要”。这当然也有交通上的原因十六世纪,西洋人从海路抵达中国,再从中国东航日本,因此,其涉足的第一块东土是中国,而非日本:如葡萄牙人于1516年抵广东,1543年抵日本种子岛;西班牙人于1575年抵中国,到日本则是1584年。连与西方世界第一次正面碰撞的时间,中国都遥遥领先于日本:由枢密大臣马戛尔尼勋爵率领的英国使团抵达广州口岸是在1793年6月,距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马修·佩里率四艘战舰,于江户湾叩关幕府的“黑船”来袭(1853年7月),还有整整60年。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西人争相以汉文介绍西学,蔚为大观。据王韬在《泰西著述考》中记载,从1552年到1674年,仅“著名”传教士便有92人,他们多埋骨中土,由这些人著述的汉文著作达211种之多。可问题是,“传教士虽然不断引进近代西方文化,但是,当时的中国人却无接受之意。传教士煞费苦心用汉文写成的东西,大多数中国人亦不加理睬”。而与此同时,由于幕府实行“锁国”政策的缘故,日本社会求洋若渴,大量洋人所著西学汉籍越境东洋,以汉译训点本或日译本的形式,进入了日本文人的书斋。如英人合信(Benjam inH obson)的医学书《全体新论》于1850年在中国付梓,1857年被伏见医生越智氏在日本翻印,翻印版次达10次之多。美国传教士丁匙良(W.A . P. M artin)著《万国公法》的汉译本于1864年在中国出版,翌年便被日本开成所翻印,后又增印数版,明治时期成为法学教科书。国人既漠视洋人著作的西学典籍,自然不会积极译介。第一本由中国人自己译刊的西洋书籍是1847年魏源的《海国图志》,但比日本的《解体新书》晚了74年。 如此,“西洋人出版各种洋书的汉译本,目的是向中国人灌输近代文化。但是,新文化的种子在中国被埋没了,到了日本才发芽、开花”。而且,日人并不满足于汉译本,开始自己翻译荷兰书籍,从而开创了所谓“兰学”,而“兰学”恰恰成了后来风气更盛的洋学运动之滥觞。洋学在日本大行其道,推动者并不限于民间学者,德川幕府也于1855年设立洋学所翻译西洋书籍,教授外国语文。后洋学所更名为“蕃书调所”、“洋书调所”、“开成所”等,成为东京大学前身。可以说,正是汉译西学的“翻墙”效应,酿成了明治维新之前一种开明西化的空气,对日本顺应时代潮流,开启现代化进程起到了某种发酵作用。以此为开端,中日两国在一系列重要环节上开始拉开距离,从制度文明到社会文化,从金融经济到教育民生,日本均领先于中国。差距较小者有5到10年(如外语学校、报纸的创设,电信、火车的应用等),普遍相差二三十年(如文字改革运动的肇始、新式国立大学的创设及杂志的出现等),差距显著者,甚至达五六十年(如《大日本帝国宪法》的颁布、实施比《中华民国宪法》早58年,日本新货币流通比民国法币的流通要早64年)。 |
一场“文化反哺”:中国留学生在日本
留学录入:贯通日本语 责任编辑:贯通日本语
相关文章
驻日大使程永华赴熊本地震灾区看望中国留学生
在日中国留学生支援组织举办新春交流活动
去日本留学有什么优势呢?
中国留学生日本盛冈市做传统美食 款待当地民众
在日中国留学生以古礼庆祝端午
日本北海道中国会举办赏樱会暨留学生支援会
外籍机长在日居留条件拟放宽 留学生有望圆飞行梦
留学生身着中国传统服装为游客展示了日本茶道礼法
中国留学生获日语辩论赛最高奖
中国留学生感悟日本倒垃圾文化
中国留学生与日本滋贺县民众愉快“插秧交流”
到日本留学的中国留学生逐年减少
日本外国留学生总人数连续三年呈现递减趋势
在日本的外国留学生被卷入网络犯罪的案件频发
“不愿出人头地”中国留学生更受企业青睐
奈良县中国留学生开始挑战学习日本古老的平民艺术
3名赴日中国留学生到日本山口县下关市访问支援企业
日媒:日本警方查处多起在日中国人利用QQ犯罪案件
日本天皇向救助日本儿童中国留学生授予“红绶褒章”
日本留美学生连续8年减少 已经不足2万人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举行仪式表彰中国留学生严俊
越南留日学生增长迅速有赶超中国趋势
中国赴日留学生两年内减少超万人
约八成在日外国留学生认为就业形势严峻
东京造型大学中国留学生纪念二战被掳中国劳工